前言
我是在23年7月份来的广东,如果说满一年才算是一篇年终总结的话,那应该是《我与文华》那篇。这篇不一样,这篇是我对2024年的总结,2024一年的感悟很多,想单独再写一篇,至于能不能称得上是“总结”,无关紧要。
如果开篇定下这篇文章的主题,那就是神圣的“二元论”,通过这一年经历的种种事情,我对它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的大学四年(其中包括了三年的疫情,被封在宿舍里好久,但有时回看那段时间写的东西也挺有意思的),我称之为被加速的大学生活,整个过程中,我少体验了很多课题,或者说是成长,导致要在未来补,我也算是理解:为什么曾有很多长辈评价我说:“你适应社会比别人慢。”刚毕业即步入社会,难免不产生一些感悟。大学的时候不涉及过多的人际关系和利益交换,当时也没想过太多。引用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话来说就是:
那时,我还没有懂得人性是如何的矛盾,我不知道真诚中有多少做作,高贵中有多少卑鄙,或者,邪恶中有多少善良。如今我是充分懂得了,小气与大方、怨怼与仁慈、憎恨与热爱,是可以并存于同一颗心中的。——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一
权力位差引发的价值补偿现象
在人际互动中,权力位差会引发价值补偿的现象。当我们将人际关系主体简化为”高位者”与”低位者”模型时,可观察到某些低位者(俗称”小人”)通过主动让渡决策权来获取关系优势的现象。其内在逻辑在于:高位者往往掌握着低位者亟需的资源或认可,这种结构性差异催生了低位者的适应性策略——暂时隐藏真实需求,通过满足高位者的情感期待获得准入许可。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关系模式中的角色定位具有流动性和场景性。同一主体在不同情境中可能交替扮演两种角色,这解释了为何针对特定”小人”的评价常呈现两极分化:既得利益受损的同侪群体容易产生负面评价,而受益的权力方则倾向给予正向反馈。这种评价分歧本质上反映了不同立场对价值交换合理性的差异化认知。
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分析,低位者的策略选择实为理性权衡的结果。当个体将短期关系收益置于自我完整性之上时,会主动强化高位者的主导地位以换取资源倾斜。这种现象在科层制组织中尤为显著,其深层机制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需求先于自我实现需求”的层级规律相契合。
说人话就是,人与人相处存在能量交换,人与人的本性也有不同,没有绝对的小和大,但是存在小和大的关系。
总有人处在关系的高处,有人暂时蹲在低处。那些被叫做“小人”的家伙,其实就像职场里的“捧哏”——他们不是真的没主见,而是算准了领导手里攥着升职加薪的门票,索性把自己的想法打包收起来,专门给大佬们递情绪价值。这类人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同一批人里,基层同事骂他们马屁精,老板们却觉得他们贴心又懂事。
这背后的逻辑特别现实:当你手里没资源的时候,生存本能就会逼着你做选择题。是梗着脖子坚持自我然后被边缘化?还是暂时当个“人形夸夸机”先混进圈子?大多数人都会本能地选第二条路。就像刚入职的小透明给总监泡咖啡,实习生追着主管改PPT,本质上都是同一种生存策略。
但千万别把这套模式简单归类成“好人和坏人”。今天在甲方爸爸面前当孙子的乙方经理,明天回公司就是被下属捧着的爷;昨天还被导师骂得狗血淋头的博士生,转头就能在师弟妹面前摆谱。我们都在不同场合切换着“当孙子”和“当大爷”的皮肤,只不过有些人换皮肤换得特别勤快而已。
这世上压根没有孤立的大人或小人,他们就像硬币的正反面。你试试把硬币劈成两半?那这钱就花不出去了。
“大人”为何需要“小人”?
当一个领导者(“大人”)的势力还小时,他可以亲自扮演“恶人”,训斥下属、施加压力、杀伐决断。但随着组织壮大,他必须塑造完美形象:仁慈、睿智、公正。可现实是,管理不可能永远温和,总有人需要被震慑、被惩罚。于是,“大人”必须培养“小人”,让他们去执行那些自己不便亲自做的“脏活”:整肃异己、施压团队、传递威胁。这些“小人”就像组织的免疫系统,专门对付那些可能危害体系的“病菌”。
好比刚创业小老板,公司就七八条枪。这时候他既是菩萨又是夜叉——白天陪客户装孙子,晚上骂员工当大爷。等熬到公司上市,突然发现人设卡bug了:现在得穿着高定西装给灾区捐款,举着香槟跟官员谈民生,哪还能亲自拍桌子指导教育?这时候就得找一个工具人。这个灌了恶念的傀儡,专门替他干些见不得光的事。你以为那些鞍前马后给领导背锅的中层是哪来的?都是老板们吐出来的”心里脏”。
最绝的是这套系统根本离不开小人。就像庙里得有阎罗殿,公司也得有背黑锅的。哪天要是把“小人”开了,员工是痛快了,可转头就会发现:大老板突然变得慈眉善目,底下人反而开始摸鱼摆烂。这就好比把地狱拆了,菩萨的香火钱都得少一半。
选小人更是门行为艺术。你以为老板会选天生坏种?虽然存在天生坏种,但不绝对,往往真正被钦点的,是长得像反派的老实人。举个栗子:现在要挑个部门“黑脸”,你是选那个纹着花臂的真混混,还是选那个长得像《九品芝麻官》里方唐镜的憨憨?当然是后者!纹身哥随时可能反水,方唐镜虽然面相刻薄,但胜在听话好拿捏。现实中,许多企业内部的中层管理者往往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看似凶神恶煞,实则是高层最忠实的执行者。这些人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可能从未想过成为“小人”,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戴上这副面具。
现在明白为什么大厂高管都爱供佛像了吧?他们心里清楚:自己白天装的每一份慈悲,都得靠夜里放出去的恶鬼来还债。哪有什么天生的恶人,不过是神仙们要立牌坊,总得找人帮忙拌水泥。
小人为何”畏威不畏德”?
小人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他们只屈服于权威,却不会被道德感化。他们精于算计,擅长窥探他人隐私,挖掘弱点,并把这些信息变成操控他人的工具——或散布流言,或暗中打压,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
初到一个新环境时,我曾反复思考:是我太温和,让人觉得好欺负,还是我目前所在环境本就如此?后来发现,这类人往往内心藏着一种阴暗的自卑,他们需要通过贬低他人来获得短暂的优越感。你的宽容不会换来感激,反而会让他们变本加厉,因为他们的生存法则就是依附强者、欺凌弱者。
他们不会真正敬重道德高尚的人,除非这个人同时具备让他们畏惧的力量。小人只认实力,不认道理。
小人的变种:”墙头草”的生存策略
在众多小人类型中,”墙头草”是最常见也最隐蔽的一种。他们看似无害,甚至表现得友好热情,实则擅长在各方势力间游走,左右逢源。他们的策略是:
暗中观察,寻找靠山——他们会迅速判断谁有话语权,然后主动贴近,建立”人脉”。
表面热情,实则势利——当你得势时,他们会表现得无比忠诚;一旦你失势,他们立刻疏远,甚至反咬一口。
擅长造势,制造假象——他们会刻意营造自己的人缘,让别人误以为他们很有影响力,从而借势压人。
如何应对这类人?
保持距离,避免交浅言深——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私事或弱点,以免成为他们的筹码。
观察行为,而非听信言语——墙头草最擅长说漂亮话,但他们的行动往往暴露真实意图。
建立自己的威慑力——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他们才会收敛。
一个环境里小人多,往往说明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则有问题——要么缺乏公平的竞争机制,要么上位者默许甚至鼓励这种行为。
在职场,如果领导喜欢听信谗言,那么搬弄是非的小人自然会越来越多。
在社交圈,如果群体崇尚表面关系而非真诚交往,那么墙头草就会如鱼得水。
我深有体会。
关键在于,你要判断这个环境是否值得长期停留。如果小人得势是常态,而你又不愿意同流合污,那么及早调整策略,或者寻找更适合的圈子,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最终解法:让自己变得难以被操控
小人之所以能影响你,往往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你的某些软肋——可能是你在意名声,可能是你害怕冲突,也可能是你过于善良。
破解的方法很简单:
减少可被利用的弱点——不轻易暴露情绪、不随意分享隐私。
培养坚定的立场——让小人明白,你不是他们能随意摆布的对象。
必要时反击——如果对方一再试探底线,适当的强硬态度反而能让他们知难而退。
小人永远不会消失,但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难被他们影响。
真正的强大,不是消灭所有小人,而是让他们不敢轻易招惹你。
二

去年中秋,我去了一趟澳门。玻璃幕墙外澳门塔的霓虹像根沾满糖霜的冰糖葫芦,让我想起大一国庆和大彭在重庆的校园里漫步夜晚——那时我们在操场散步,发誓要混出人样,而今他已是澳门大学实验室里泡了一年多的”老彭”。
横琴口岸的麦当劳里,那个穿花色短袖抄着裤兜的身影让我恍惚回到高中教室后门。大彭还是那样,只是金丝眼镜后多了几道熬夜的血丝,同时内在有了这个年纪每个人都该有的那份成长。“实验鼠今天放假。一会带你去澳门溜达。”高中时我就跟着他玩,带我认识好多新鲜事物,这次又有了同样的感觉。
威尼斯人的运河会倒流时光,人造天空的云朵永远停在文艺复兴的黄昏。当贡多拉船夫唱起《我的太阳》时,大彭正教我如何在赌场生态圈优雅白嫖:奶茶,蛋挞,把发财车当观光巴士坐。

新葡京像座巨型呼吸着的器官。水晶吊灯是肺泡,轮盘是心室,二十一点牌桌是舒张的瓣膜。大彭带我破解赌场设计的风水细节:地毯花纹是扰乱判断的迷宫阵,天花板镜面会折射焦虑情绪,连香氛系统都掺了薄荷味让人保持亢奋。当我们捧着免费奶茶穿过无窗长廊时,他敲敲墙壁:“这是吸音棉,吞掉所有时间流逝的声音。”
澳门没有田,只有庄和闲。不同于内地的纸醉金迷,那是另一种制度下的富有。当我看到了白发苍苍,衣衫陈旧,手拿筹码盯着赌桌思考的赌徒时,突然明白了这座城的生存法则——这里的土地不长稻谷,只长欲望的菌丝。赌场穹顶永远笼罩在人造暮色里,白发老头攥着筹码的样子,活像庙里攥着香火的信徒。只是菩萨不喝红酒,而这里的庄家端着拉菲在监控室里看人间。
在这地方,所有欲望都会被加工成筹码。娱乐城里面的游戏很简单,大部分游戏规则稍微研究就能学会,赢和输的概率大都是一半一半,充满了让你试一下的诱惑。不怕你赢,就怕你不玩。他们卖的根本不是胜负,是让你上瘾的幻觉。澳门真正的赌局不在桌上——在你相信运气可以战胜概率的那一刻,就已经输了。
当殖民时代的葡式碎石路遇见横琴新区的玻璃幕墙,这座城市的魔幻现实恰似它的双面赌桌——一面刻着《澳门组织章程》的陈旧纹路,一面映着基本法的金色天平。四百年前葡萄牙商船卸下的不仅是香料箱,还有总督集权的政治骰盅。那些年澳门人押注命运,却连查看赌局规则的资格都没有。直到1999年庄家易主,我们才真正看清赌桌的全貌:严谨的算牌师把殖民时期227项混沌法令梳理成保障权利的54部基本法律;曾经总督独揽的骰子,被拆分成立法会的象牙球、行政长官的金色秤杆和终审法院的水晶骰盅。
如今走在议事亭前地,土生葡人后裔手机里播放着《七子之歌》,腕间却仍戴着祖传的葡式银镯——这或许就是“一国两制”最精妙的赔率设计:既不用掀翻历史赌桌,又能让每个筹码都落在宪法框定的红绒布上。当港珠澳大桥的霓虹照亮黑沙滩,当年被当作赌注押上的25.8平方公里,正以举世罕见的政治赔率,兑现着“马照跑,舞照跳”的庄家承诺。
然而,澳门的年轻人却常常在这种巨大的制度福利和经济诱惑下,感受到不小的压力。特别是在高房价的困境中,年轻一代的生活逐渐趋向焦虑。在澳门,房价的高企已成为许多本地年轻人最大的不安根源。年轻人面对的,不仅是追求职业与家庭平衡的挑战,还有如何在这座繁华的城市中扎根的难题。尽管澳门在福利政策上做了许多努力,比如提供健康保险、退休金制度,以及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等,但面对日益攀升的房价,许多年轻人依旧感到“安家立业”的梦想遥不可及。
澳门的房价问题,背后是这座城市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所带来的复杂后果。经济的飞速发展与高房价之间的矛盾,让许多年轻人陷入了“虽然生活在这座繁华城市,却始终无法享有城市生活”的困境。虽然他们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更广阔的职场空间,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如何维持一份安稳与幸福,往往取决于你能否在这片土地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从《澳门组织章程》到基本法,从总督集权到行政主导,这场跨越四百年的制度变化证明:文明的迭代既需要破茧重生的勇气,更依赖春风化雨的智慧。那些嵌在市政署瓷砖画里的葡萄牙帆船,终将成为后人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标本。
就像大三巴牌坊在炮火中熔铸出中西合璧的浮雕,澳门回归前后的制度变迁,恰是中华文明吞吐八面来风的当代显影。那些写在基本法序言里的承诺,终将在横琴岛的试验田里长出新的年轮。
当港珠澳大桥的钢索牵起珠江口两岸的晨昏,澳门的故事早已超越简单的二元叙事。这座用筹码构筑欲望迷宫的城市,正用“爱国爱澳”的底色证明:制度的生命力不在于非此即彼的对抗,而在于海纳百川的兼容。
三
也许是受大环境影响,一段时间里,媒体给我推送了好多关于地缘政治的视频。每晚回家,一边吃饭,一边了解中东那边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补充了我对世界局势认识上的不足。
谈论政治总是离不开经济。
世界经济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博弈,繁荣与衰退、增长与萧条、通胀和通缩,彼此对立却又相互依存。当一国经济高速发展时,另一国可能正陷入滞胀;当华尔街的股市屡创新高时,某个新兴市场可能正遭遇货币崩盘。这种不平衡并非偶然,而是资本流动、政策选择、国际分工共同作用的结果。
回顾历史,经济差距往往是冲突的根源。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二战,2008年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动荡。经济全球化让世界更紧密,但也让强弱之间的鸿沟更加明显——强者制定规则,弱者被迫适应,甚至沦为牺牲品。
美国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掠夺+金融霸权”的教科书。19世纪,它靠奴隶制积累原始资本,靠西进运动掠夺土地,靠工业革命奠定制造业基础。20世纪,二战后的美国,凭借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再通过石油美元、华尔街投机、跨国公司扩张,构建了一个“金融帝国”。21世纪,美国的繁荣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股市、债市、衍生品交易,而制造业却不断外流。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变成了废墟,硅谷的科技巨头却富可敌国。
当资本只追逐短期利润,谁还会去建设实体经济呢?美国的芯片法案、制造业回流政策,恰恰说明它已经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危机。但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只要东南亚的劳动力更便宜,华尔街就不会把工厂搬回俄亥俄州。
与美国不同,中国走的是一条“市场换技术+自主创新”的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用廉价劳动力和庞大市场吸引外资,成为“世界工厂”。21世纪后,中国不再满足于代工,而是通过政策引导、科研投入,逐步掌握高铁、5G、新能源等核心技术。今天,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螺丝钉到空间站,都能自己造。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不依赖金融霸权,而是靠实体产业支撑经济增长。即使遭遇贸易战、科技封锁,仍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21世纪的经济,越来越像一场“金融炼金术”——钱生钱,债叠债。美股十年长牛,但背后是美联储的无限印钞和公司回购股票推高市值。加密货币狂热,比特币一度冲上10万美元,但没有任何实体经济支撑。附上《华尔街日报》资深市场专栏作家 James Mackintosh 发文讲比特币的文章,我觉得写的不错。恒大暴雷,2.4万亿债务背后,也是房地产过度金融化的恶果。
当一片欣欣向荣时,谁也不会注意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就可以打破这个梦幻泡沫。
东北人骨子里刻着“未雨绸缪”的基因,更早明白繁荣的脆弱性。小时候听长辈讲下岗潮,总以为那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叹息。很多80后90后早早就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离开家乡。当”振兴东北”的标语逐渐褪色成粮仓基地的底色,00后的我也带着”宇宙的尽头是东北”的自嘲南下广东,这句话里的无奈只有东北人才能明白。
疫情前的生活状态,似乎每个人都在奔跑着追求更高的生活标准。那时,大家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觉得社会的进步、科技的飞跃,能够让每个人从中受益。疫情的到来,让这种繁荣的错觉骤然破灭。2020年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全球经济处于停滞中,工厂关闭,商业活动暂停,人们的生活突然变得不确定。那些原本看似稳固的行业,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疫情后的生活,所有人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生活被打乱的同时,也逼迫人们思考:我们该如何定义真正的自由?22年末,我有幸第一时间体验到了ChatGPT,感到惊艳的同时也多了一分恐慌。AI与自动化逐渐成为未来的关键力量,但它们又能为我们带来多少解放?像ChatGPT这样的工具,似乎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人的创造力和自由似乎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更高的升华。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轨迹,意识到个人的财富和自由,可能并不只是依赖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更可能通过理解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变化来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
2024年8月下旬,我的左眼皮一直跳,持续了一周。那时候,工作上略显焦虑,身体也在悄悄反应。这种小小的不适,提醒着我,也许应该静下心来反思一些事情。一天晚上,我读到了一篇研报,突发奇想买了两只股票,然后赶上了9月美联储降息的利好消息,眼看着A股大盘从2800多点涨到了3400点。这一波涨幅让我赚了一些钱,但这笔意外之财并未让我感到过度兴奋。相反,它让我多了一层思考:当人类依然需要通过劳动获得发展的当下,财富自由似乎成为了更直接的目标。是的,虽然距离真正的财富自由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通过这次经历,我意识到:或许我应该先达到财务上的自由,再去追求自己心灵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去体验更深层次的自由。
当所有人都在股市、币圈、楼市里投机,谁去真正创造价值?金融可以繁荣一时,但债务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膨胀,直到破裂。
今天的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美国想“去中国化”,推动制造业回流,但资本却更愿意去越南、印度。中国推进“内循环”,但完全闭关锁国不现实,仍需参与全球分工。欧洲深陷能源危机,被迫重新依赖煤炭,绿色转型遭遇挫折。
最终,经济规律不会说谎,金融可以制造虚假繁荣,但真正的国力依然取决于科技、制造、能源自主。债务可以拖延危机,但无法消除危机——2008年、2020年的崩盘就是明证。未来的竞争,不是比谁的股市涨得快,而是比谁能更好地平衡虚拟与实体、资本与劳动、债务与增长。
文明的根基,仍是劳动与创造。
无论AI如何颠覆金融,无论元宇宙如何虚拟化世界,人类社会的根基依然是资源、粮食、能源、技术。迪拜的哈利法塔再高,也需要工人一砖一瓦建造。经济可以虚拟化,但文明不能。
当资本狂欢时,别忘了,真正的财富,永远来自人的劳动与创造。
五

这一年的经历就像是一次不断旋转的旋涡,既有前行的力量,也有回望的迷雾。在繁华的背后,我们每个人都在与无形的力量博弈,无论是职场中的职权争斗,还是人际关系中的微妙权衡。每一步的抉择、每一次的冲突,都是成长的契机。
感谢这一年中,那些包容我、帮助我成长的人。无论是善意的扶持,还是带着挑战的考验,它们都成为我前行的力量。有人给我带来温暖,有人带来伤痛,但正是这些对立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强,帮助我在混沌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世界总是如此,永远在阴与阳、左与右、繁荣与衰败、善与恶、希望与绝望之间相互交织。这种二元对立的存在,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充实、更加复杂。正如螺旋上升的轨迹,只有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我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才能在平凡中寻得非凡,在纷杂中保持清醒。
回望这一年,或许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在风雨中挺立的种子,在阳光下会蓬勃生长,甚至在某些看似“黑暗”的时刻,也在悄然汲取着养分,向着属于自己的方向茁壮成长。正如那句古话:“世界如此广阔,人生百转千回,我们终将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行。”这一年的经历,也让我更加坚信,无论怎样的风雨,最终都能让我们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作词: Childress, Roland
作曲: Ed Roland / Ross ChildressHas our conscience shown?
我们还有没有道德心?Has the sweet breeze blown?
还有没有清甜的风在吹着?Has all the kindness gone?
这世上还有没有善意?Hope still lingers on.
残留的希望还在逗留着I drink myself of newfound pity
我用遗憾灌醉自己Sitting alone in New York City
独自坐在纽约城里And I dont know why.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Are we listening
我们在听着那些..To hymns of offering?
为给予而唱的赞美诗吗?Have we eyes to see
我们的眼睛还能看到..That love is gathering?
爱在聚集吗?All the words that Ive been reading
我读过的所有的词句..Have now started the act of bleeding
都开始流血Into one.
互相渗透Into one.
融为一体So I walk up on high.
所以我走向高处And I step to the edge
立于边界之地To see my world below
看着下面的世界And I laugh at myself
我开始嘲笑自己..As the tears roll down.
在眼泪滚落的时候Cause its the world I know.
因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世界啊Its the world I know.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世界啊I drink myself of newfound pity
我用遗憾灌醉自己Sitting alone in New York City
独自坐在纽约城里And I dont know why. Dont know why.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So I walk up on high
所以我走向高处And I step to the edge
立于边界之地To see my world below.
看着下面的世界And I laugh at myself
我开始嘲笑自己..As the tears roll down.
在眼泪滚落的时候Cause its the world I know.
因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世界啊Its the world I know.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世界啊Yeah I walk up on high
因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世界啊And I step to the edge
所以我走向高处To see my world below.
看着下面的世界And I laugh at myself
我开始嘲笑自己..As the tears roll down.
在眼泪滚落的时候Cause its the world I know.
因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世界啊Its the world I know.
The World I Know (LP Version)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世界
Peace & love
❤️❤️❤️
2025年3月30日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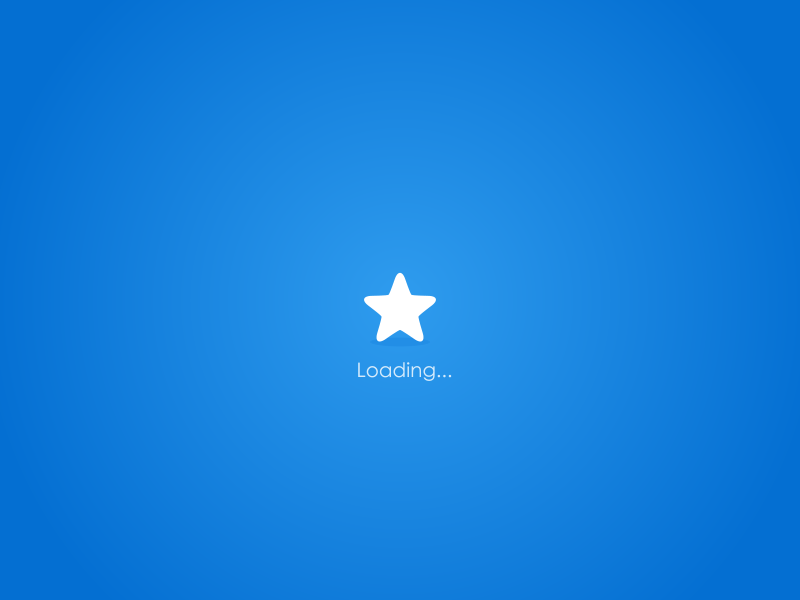

评论(4)